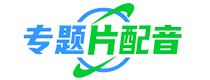敦煌之守望敦煌大型电视纪录片解说词配音
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孕育的敦煌灿烂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古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生机勃勃,就像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

这段影片记录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后重庆的那个令人陶醉的夜晚。多少中国人尽情地流淌着他们压抑了八年的欢笑和泪水。在这些蹦跳的人群里就有国立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段文杰。战火余生,大批滞留在重庆的外乡人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而身为四川人的段文杰却告别了新婚的妻子,随着喧闹的人流,他要向北、向西,去他向往已久的敦煌,与神灵和艺术对话。
“并不仅我一个人,去的人是很多的。比如说张大千就去得很早的,他也到那去住,住了很长时间。许多人都去了。”段文杰辗转了一个月到达兰州之后,听到的却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撤消的消息,在兰州他见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常书鸿对他说,为了研究所的生存,我必须去趟重庆,前途祸福难测,你千万不要等我。1946年的冬天,人们在兰州街头经常看见一个卖水的小伙子,那是段文杰在黄河岸边翘首东望,他在这里已经等候一年了,他坚信常书鸿会回来的。就是这个冬天,他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等来了被段文杰的执著感动得满眼泪水的常书鸿。
“到家了,伸手就可以摸到最蓝的天,低头就可以看到风沙吹乱的群山。”从那一刻起,段文杰再也没有离开敦煌。没有一天放下过画笔。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人称为“大漠隐士”,成为蜚声世界的敦煌学权威。
“我最喜欢的是,随便哪一幅我都喜欢,在洞子里头都亲近得很好。“你看从常书鸿先生创办这个所,来的都是一些画画的人,他都抱着什么想法,我到这儿来学习古代绘画。那么学习古代绘画的方法或者说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临摹。”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全部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壁画临摹,和段文杰同时期到来的几位画家大多来自四川,和四川的雨雾天相比,敦煌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太阳。欧阳琳刚来的时候只有23岁。
“美丽的天空,白天太阳出来过后,只要有太阳天蓝,蓝得很,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个老工人他会种瓜,种的甜瓜,种的相当好。我们大家虽然是其他的饮食不太好,但是瓜果非常好的。”如果说大漠的风情让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忽略了饮水困难、缺乏蔬菜的种种不适应,那么他们从事的壁画临摹工作也让人不再有与世隔绝的孤独沉闷。“我一进洞我的精神就来了,里面有好像看不完的东西,什么都想看,我都需要。”
这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形象,让年轻的艺术家们神游物外。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此时的敦煌研究所开始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到1948年初,他们绘制了壁画摹本八百多幅。“当时我们就临摹些小的东西,小的图案啦或者飞天啦菩萨啦,菩萨头像啦,当年就是临摹这些小品。”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

从1943年常书鸿带领着第一批志愿者龚祥礼、董希文、张琳英等十二人来到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又有自愿来敦煌的段文杰、郭世清、沈福文等八人;1948年,周星翔自费来敦煌临摹,史苇湘从四川来敦煌。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一批批年轻人的到来给敦煌带来了生机,给敦煌艺术的传承带来了希望。“敦煌艺术的魅力我觉得在什么条件之下都可以处下去,就这么简单。”敦煌的石窟艺术究竟是什么,在今天依然享受着智慧果实的人们自然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树开了这花结了这果实。又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这些艺术家前赴后继,甘愿相守。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日,很多敦煌人会按照他们的世代传统,来到寺院或者莫高窟朝圣礼佛。这一天也是莫高窟聚集敦煌当地人最多的日子。敦煌城的老百姓有很多对佛教怀有信仰,这里面有这座城市本身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原因。在佛教刚刚从印度进入中国河西走廊时开始,敦煌就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算起来,这座古老的城镇经受佛教的洗礼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了。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地方之一,以及敦煌当时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佛教很快在敦煌生根发展。正是佛教的发展促进了一大批石窟艺术的产生。从公元366年乐僔法师在敦煌开凿了第一座佛窟开始,到唐代已有一千多座大大小小的满是壁画和彩塑的洞窟。一个时代它必须要有大作,这个大作在哪呢?
“当时的画在寺院里面了,画在那个殿堂里面,当时肯定是有很多宫殿建筑,放在那个里面。然后就是寺院,然后就是石窟。敦煌是幸存的东西。”这些被称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大作的壁画、彩塑,带给观者的震撼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那位曾经因盗取莫高窟壁画而臭名昭著的兰登.华尔纳在传记里写道,“神佛们是那样地高深莫测,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我会远涉重洋横越亚美来弄清楚他们的存在。着非凡的美已让我无法使自己带着批判的眼光从事研究。我并非佛教徒,但此时却领受了一次神佛的洗礼。”
自从公元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就一直牵动着世界的目光。人们很难找到还有第二个地方能像他这般凝聚着连绵的历史和不断中断的文明,像她这般让全世界的学者痴心不改并以身相许。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紧紧相随。
段文杰先生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在他模糊的的记忆里,记得最清楚的永远是洞窟,是他临摹的画。段文杰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半生主要致力于敦煌壁画的临摹,后半生倾尽心血从事敦煌学的研究。他为壁画临摹定下的原则是:客观再现原作面貌,要突出原作的神韵,绘画技巧不能低于原作水平。他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2007年9月22日在为段老90岁生日举办的画展上,人们看到了他的身影和他的作品。就是这幅段文杰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于1958年和同事们临摹的上百幅壁画在东京展出,这是敦煌壁画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从此,日本源源不断的赶赴敦煌朝圣礼佛的旅游活动开始了。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著名画家平山郁夫说,敦煌保存着日本文化的精髓,是日本文化的故乡。这里是北京国家图书馆三位来自英国的朋友正在给工作人员传授怎样用电脑技术修复敦煌的经卷。“这是我们来自伦敦的摄影师,他会给你们讲怎么做敦煌文献数字化,整个这个过程。”

近年来英国图书馆联络中国、法国、俄国等国家的收藏机构成立了国际敦煌学项目,它是利用高新科技把各个国家收藏的敦煌文书输入电脑,供世界各地的个人和机构使用,广泛进行国际间的交流合作。这些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书出自于敦煌藏经洞。当20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一扇历史之门就在敦煌被一个小人物打开,王道士的偶然发现使石窟宝藏重见天日。他的发现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和它的历史王道士自己是浑然不知的。
1909年北京的一个胡同里,以罗振玉为首的中国学者们在全力以赴地抄写伯希和从敦煌拿走的文物,中国人抄写属于中国的经卷,作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悲凉可想而知。敦煌遗书的精华流失到了海外,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中国学者追寻海外文物的过程。2007年11月10日著名学者王国维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正在纪念他在中国历史文化学术上的贡献。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和敦煌遗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老师罗振玉从抄写经卷的第二天就开始写《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的文章,首次公开向国人介绍了敦煌宝藏及发现的情况。
1911年的冬天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王国维跟随罗振玉举家东渡扶桑,在日本京都一住就是八年,他们闭门治学,埋首于敦煌遗书和甲骨文的整理研究之中。“那是1912年以后的事情,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国际敦煌学的摇篮期的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有人说,要想做一部目录索引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网罗齐全几乎不可能。
1981年,一位日本学者在兰州作演讲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深深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灵。1978年的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航程,敦煌学的早春天气终于来临。198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石窟,问起敦煌文物研究所今后的打算,所长段文杰回答说,敦煌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保护,常书鸿先生带领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转到敦煌学的研究上来。邓小平说,外国人搞了几十年敦煌学,我们落后了,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人们对敦煌研究院的几代领导人都有一个称谓,常书鸿被称为是“敦煌守护神”。“照相,来,我们俩照个像,老搭档。”段文杰是“大漠隐士”。对这位看上去娇小的上海女性,人们叫她敦煌的女儿,她就是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
提起她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有很多钦佩也有几分惧怕。“这个樊锦诗就是七情六欲有毛病也有优点,但是工作还应该说是认真的,毛病也不少,就这么一个樊锦诗。”人们称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不仅因为她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长度,更是因为她对敦煌投入的情感。樊锦诗说,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
在洞窟几乎天天能看见樊锦诗的身影,对每一个洞窟的壁画和塑像她如数家珍。“正襟危坐专心一致,然后呢特别好的表现就是说他笑。猛一看他并没有笑,仔细一看要我说他的脸上到处都在笑。他就妙在哪儿呢?微笑含蓄地笑,他不是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很夸张的,他的笑出自内心的。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眼睛略微有点眯,眉毛有点挑,鼻翼有点张,嘴巴两角有点翘。”

莫高窟这个绝世宝藏竟曾被充当监狱。1920年一批在十月革命中流亡出来的白俄官兵窜入中国境内,被中国地方政府扣留,就关押在这里。第427窟这些面目全非的壁画是白俄囚徒留给莫高窟的记忆。壁画上的金箔被刮走,留下的是斯拉夫语的下流话,第156号洞窟还有烟熏火燎的痕迹。1943年的藏经洞早已空无所有,因为西方探险者的盗窃,再也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是藏有五万卷经卷的文化宝库。(常书鸿日记)“这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顾着她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它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负在我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沉重啊!”
1944年,这天清晨,在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南边不远的一个院落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终于结束了四百多年来在民间缺乏有效管理的状态,第一次蒙受国家、政府的庇护。这一天是1944年1月1日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常书鸿日记)“院中有两课栽于清代的老榆树,院中正房是工作室,北面是办公室和储藏室,南面是会议室和我的办公室。大家都在研究所办的食堂吃饭。虽然没有硬性规定工作上下班时间,大家都十分自觉,饭后早早进洞子临摹、调查,各干各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人员不超过十人,那时常书鸿不断给内地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很快董希文、张琳英、李浴等一些内地年轻的艺术家陆续来到敦煌,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常书鸿的学生。
“那个戈壁滩真是天连地、地连天一望无际,就像你坐个小船在大海里头。所以那时候就说,不到河西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个厨师就给你端来你四个人四碗面条,就这样没别的,就是一碗醋一碗盐,你就面条一勺醋一勺盐,拌一拌就吃了。那生活都挺艰苦的”不久,常书鸿说服妻子带着一对儿女从重庆来到敦煌。“常书鸿老师的爱人打扮得很漂亮,长得也漂亮,她也爱打扮。”
考察洞窟、研究美术史、临摹壁画,相对于战火纷飞的前线,平静的西北荒漠反而为艺术工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晚唐五代时期的千佛洞,文献记载有过十余个寺庙,二三百个僧人的盛大规模,经过四百多年的沉寂之后,这段日子应该是千佛洞大事记中又一个重要时期。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敦煌,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很多著名的人物。1943年4月,就在敦煌春色最浓的时候,张大千完成了在莫高窟的临摹,收拾行装离开千佛洞。张大千将一个纸卷交给常书鸿,那是一幅“采摘蘑菇秘密地图”,上面标明在敦煌哪里可以找到蘑菇,此后的若干年,这张地图为常书鸿他们单调的餐桌增添了不少稀罕的内容。张大千原本打算只在敦煌逗留三个月,他离开的时候,已恍然过去了近三年。
期间他们共临摹壁画二百七十六幅,这些画作不但对他以后的画风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莫高窟大规模维修时,其中近二百幅作品被借用参考。为了此次敦煌调查研究,张大千除出售大量自己的作品和心爱的古代书画藏品外,还先后借债五千两黄金,这在当时相当于五百根金条。当1943年11月张大千一行返回成都时,友人注意到,张大千走时须发如漆,归来已耳鬓染霜。(常书鸿日记)“我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上百个洞窟已被流沙掩埋,虽然生活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工作情绪都很高涨。我们雇了少数民工,加上我们自己,在洞窟外面要修建一条两米高、两千米长的围墙,把下层洞窟的积沙推到0.5公里外的戈壁滩上。此外,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和修路、植树,这些工作我们整整大干了十个多月。”

秋天来临,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到莫高窟已经半年多了,艰苦的环境简陋的条件不断考验着他们。“临摹的颜料也成问题,我记得用马力牌的广告色,但是有些矿物颜色都是当地的那个泥巴非常好,那时候就把它泡开了,就当那个颜色。”“从刚来就吃大泉河那个水,咸水,别人刚一来就是吃那个,我们吃习惯了。别人以来吃那个水就拉肚子,意志不坚强的人根本就呆不住。”经费困乏,条件简陋,使过去长期习惯于艺术单纯的常书鸿不得不面对许多现实而芜杂的问题。
“我父亲很压抑,回到家里对我母亲不是很好地安抚关怀,而是发泄,跟我母亲吵架。一点的事,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我母亲受不了了。”“所以这样子就促使两个人感情慢慢慢慢…”。一天,常书鸿的学生把一些信件交到他手里,他的妻子不辞而别。常书鸿连夜追到安西,问遍了车站、旅店,也没有找到出走的妻子,最后总算打听到消息,失望和疲惫中,常书鸿继续向玉门方向追去……。(常书鸿日记)“后来才知道,我是被戈壁上找有的人救起的,经过急救和三天的护理才恢复过来。”抗战胜利的消息,一个月之后传到敦煌,人们在欢庆喜悦之余,思乡之情油然滋生,八年了,谁不想回家看看啊。“都要走,凡是这些研究人员都走了。”
这时候的莫高窟,一片冷寂。不久又一个消息传来,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抗战胜利百废待兴,为节省经费,裁撤一切“不需要”的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撤消。(常书鸿日记)“今天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死沉沉阴森森的,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狼嗥。这样的夜本来是已经习惯了的,可如今却是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成寐。那些熟悉的壁画和彩塑,当我一来到千佛洞,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与它们融化在一起。我离不开它们”
“卖家里的东西,我亲自给卖的,到城上寄托到一个商店里去卖的。当时那些做买卖的人都说,哎呀,你们常书鸿都穷成这样了,连路费都没有,就把好衣服啊,西装皮靴啊,他法国穿过的好衣裳都卖掉,当路费回去。”1945年冬天,常书鸿告别工作了三年的敦煌,带上一双儿女,到重庆奔走呼吁。“感觉不想离开千佛洞,看那样子眼泪花都流啊。他说你们要好好保管,把这个洞窟一定要保管好,我还要回来的。不是我去不回来了,我还要回来。当时,我们都很感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忙碌混乱,政府机构忙着回迁,熟悉的朋友劝常书鸿一起返回内地,但他却决意要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
此时很少有人顾及西北敦煌的前途命运,经过近一年的四处奔走,常书鸿最终说服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批准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拨发卡车一辆、物资若干。1946年,常书鸿带领着他新招收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四川国立艺专的段文杰、霍熙亮、孙儒僴、欧阳琳等许多学生回到敦煌。第二年,更多的人来到敦煌,其中包括重庆国立艺专的学生李承仙,她是常书鸿的新婚妻子,后来的几十年她与常书鸿相濡以沫,相伴终生。
“现在二百多个洞窟都可以登临巡视了,最近又做了一个总窟门,近来已绝对禁止两项过去已成习惯不合理地方法。一是研究所同仁不能假借任何理由有印模与喷水之行动,违则撤职离所。二是外来研究人员如发现上述行动,立即撤销研究许可证,停止其研究工作。我想一切爱护敦煌壁画的人都应该一致反对这种对壁画谋杀性的行为。”
1948年之后,敦煌的保护管理虽开始走向规范,但莫高窟历经千年,早已残破不堪,为此常书鸿曾多次向政府提请拨款修复。这个愿望,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在国家的支持下,莫高窟全面的抢救性修复保护工作正式展开,1956年和1963年先后两次对莫高窟南区进行了加固,敦煌的保护工作,由留守式的看护性保护,进入了抢救性加固保护的阶段。

抹去半个世纪的风沙,敦煌从岌岌可危的残壁危崖逐渐焕发出生命的光彩,而它的守护者已鬓染霜雪。1982年,守护敦煌40年的常书鸿依依作别,迁居北京。这是1987年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83岁的常书鸿最后一次回到敦煌。“当时我父亲总是觉得客居北京,他病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将来死要死回敦煌啊,这是他的一个遗言。”
1945年从敦煌归来一年的向达开始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向达以目录学和历史学著作等身。日本投降后他曾开列详单呼吁国民政府向日方索赔战时中国文物的损失。
张大千1949年离开大陆,这位东方画家,最终奠定了他世界级大师的地位。有人研究了张大千一生的作品,认为他的画风在45岁左右有一个重要改变,其笔墨间摆脱了清新俊逸,开始呈现出瑰丽雄奇的气象。
敦煌文物考察之后,王子云开始调转自己的艺术走向,最终把美术考古作为毕生的事业。这位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先驱渐渐被人淡忘,他成了一个学者。1990年九十四岁的王子云在书桌前长逝。三危山脚下,面朝九层楼静静的一群墓碑,是常书鸿和许多去世的敦煌工作人员的归宿。
日本作家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先生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能再一次投胎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一切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
下一篇:已经是最后一篇